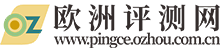海涛评论:不妨“比烂” 世界热讯
孔乙己最近又火了一把。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在鲁迅小说里可以被任何人嘲讽的孔乙己,成了一个嘲讽一些年轻人“眼高手低”的标签。
这充分说明,《孔乙己》具有文学经典的气质。这种气质至少有两个特征——
一个是,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、涂抹、误读或歪曲,从而发散出新意。比如胡子花白的孔乙己被与现在的某些年轻人相提评论,纯属歪曲。
一个是,常读常新,在不同的时代能读出不同的味道。比如《孔乙己》,在1919年读与在1959年读以及2019读,味道会有所不同。
我就是最近重读了《孔乙己》新感受,与当年在课堂上读的感受大相径庭。
小说《孔乙己》写于1919年,里面的故事发生在“20多年前”即1889年-1899年之间,是4文钱一碗酒,1文钱一盘茴香豆的时候。这个年代,姑且称为“孔乙己年代”。
在“孔乙己年代”,太平天国制造的创伤已经基本愈合,革命的烽火尚没有狼烟四起。华夏大地正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但社会秩序依然正常,社会结构及运营方式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。
4文钱一碗酒的时代很早就被定性为落后愚昧的时代了,正如曾经身处那个时代的鲁迅,将那个时代描写得灰暗、凋敝、僵化。
然而,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等到鲁迅写出《孔乙己》的时候,一碗酒已经涨到了10文钱;等到《孔乙己》发表若干年后,即连年的战争、饥荒、动荡之后,更多的小说家才发现,原来“孔乙己年代”是很多底层人可望不可求的田园牧歌时代。
从陈忠实1993年出版的小说《白鹿原》里,从王跃文2022年出版的小说《家山》里,你可以读到“孔乙己时代”的背影——那是一个礼崩乐坏之前的时代。在那个时代,读书人是被尊重的,因为科举尚未废除;私有产权是天经地义的,因而佃农与地主可以和谐相处。
一个时代好不好,其实身在其中的人往往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比如,我多年前总“对现实不满意”,现在却越来越理解很多人怀念那段时光。这就可以理解,为何与具有革命气质的鲁迅相比,后来的陈忠实和更后来的王跃文都显得“保守”——由于时间的拉长,陈、王看到了更多,有了更多参照,便不像那么决绝地否定孔乙己时代了。
再读《孔乙己》,我觉得孔乙己就是一个已过中年、生活无望、得过且过、躺平等死的人。当下的人,如果重读一遍《孔乙己》而不是凭借中学的课堂记忆“涂抹歪曲”的话,是没有理由拿孔乙己来嘲讽甚至羞辱现在“不思进取”的年轻人把考试多年获得的学历当成“脱不下来的长衫”。
原因有二——
首先,孔乙己并没有“学历”,他既不是被文凭所累放不下身段,也称不上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——他连个秀才都不是,更像一个高考落榜生。他但凡有个秀才的“文凭”,不至于喝4文钱的酒还要赊账,更不会因为经常偷窃被打,最终被打断了腿。
其次,孔乙己根本就不是个年轻人,“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”,长衫“又脏又破,似乎十多年没有补,也没有洗”,说明其已经过了中年。
总之,用孔乙己的形象嘲讽现在的年轻人“把学历当成下不来的高台”,孔乙己和鲁迅都会觉得莫名其妙。
孔乙己被打断腿,被社会淘汰,与读四书五经学八股文章没必然关系,与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必然关系。
在孔乙己的时代,依然有人金榜题名,你不能因此说读书人都会有出息,在孔乙己时代,一定有大量的人名落孙山,你不能因此说读书都会让人变迂。
总体上,每一代人都被时代的洪流所塑造,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。但是,一个人混得好不好,都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自己的原因。
混得好,就说是完全是他个人努力所致,是不公允的。混不好,就说完全是他个人不努力所致,也是不公允的。
30年前,本科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轻松进入体制内,如今硕士毕业想进体制内会被严苛的考试挑来拣去——然后他们不去收废品、卖豆腐、送外卖就被嘲讽成了“眼高手低”的孔乙己,这一边是误读《孔乙己》,一边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这样的嘲讽必然会遭到嘲讽。
总体而言,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都有些惨(除了富二代)——因为年轻,他们还没资格掌握社会资源。有些好为人师者,拿孔乙己嘲讽现在的年轻人,是因为他们多少有点既得利益罢了,而且把自己的那点“成功”归功于了自己我奋斗,不承认那更多是时代的“赏赐”。
鲁迅确实把孔乙己写得很不堪,但是孔乙己最多算是科举制的炮灰,毕竟没有成为战争的炮灰,相对于后来的很多人来讲已经算是幸运儿了。
有些人把现在一些年轻人躺平啃老说得很不堪,但人家毕竟啃的是自己家的老子,比起有些年代的年轻人拿起刀枪互杀或分别人家的田产房屋而言,实属文明,也算幸运地遇上了好时代。
有时候,不妨用“比烂”的方式鉴定一个年代。
- 海涛评论:不妨“比烂” 世界热讯 2023-03-28
- 全球即时看!巴克莱:维持苹果“持股观望”评级 予目标价145美元 2023-03-28
- 天天资讯:世界首个混合级联特高压换流站完成交流电网短路试验,可靠电力供应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023-03-28
- 全球热头条丨杂粮一次性蒸好放冰箱冷冻还是冷藏 2023-03-28
- 环球观察:京沪杭等地近期明确将有序放开设摊、允许外摆 2023-03-28
- 樊杰_天天讯息 2023-03-28
- 世界今亮点!12306积分兑换车票 1积分兑多少钱 2023-03-28
- 当日快讯:神火股份:煤炭 电解铝等产品量价齐升,2022年年归母净利同比增133.9%至75.71亿元,拟10派10元 2023-03-28
- 【环球新要闻】如何用低代码搭建训练一个专业知识库问答AI机器人 2023-03-28
- 【环球速看料】中国医学教育的问题,一是学制太长,二是这么长的学制里,临床的时间相对还是少… 2023-03-28